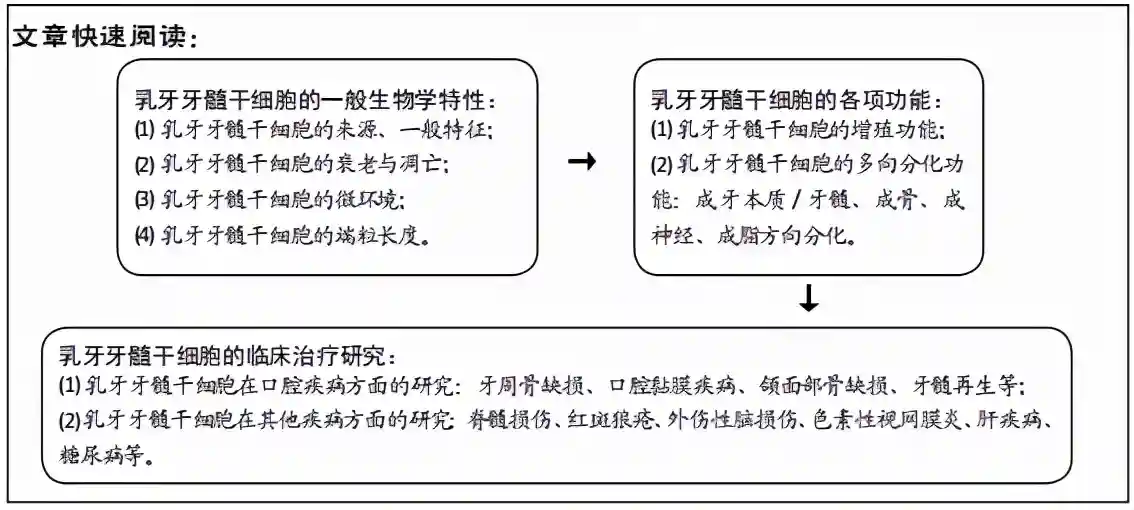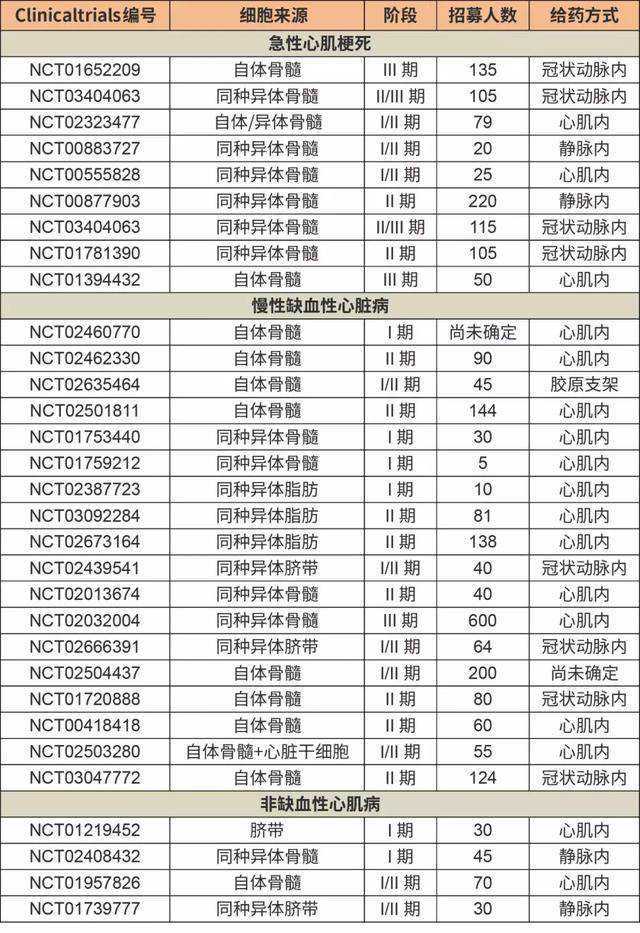3D打印器官,或者其他生长或修复器官的技术,也是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不过我个人认为,异种移植更接近于现实。
2017年9月《科学》杂志封面。该期杂志刊登了关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迷你猪身上的应用。
基因编辑对异种移植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目前正在研究对迷你猪进行大量的基因编辑,包括去除猪身上存在的α-gal糖残留(人类对其有天然抗体)。我认为,最终我们能够产生与任何特定受体紧密匹配的迷你猪供体,从而减少或者尽量减少移植后对免疫抑制剂的需求,实现成功移植。同时,基因编辑在干细胞分化和操作方面的表现将是强大的。我认为,对于像1型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最终可以将干细胞操作成与受体匹配的β细胞,注入到缺乏这些胰岛素分泌细胞的1型患者体内。
与医学其他领域的不同:
器官移植从死亡开始
新京报: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器官移植?
约书亚·梅兹里希:我认为,器官移植是过去100年中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对我来说,成功移植器官的能力(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就像把人送上月球一样。
现在,人们愿意谈论关于捐献的许多问题,包括谈论什么是死亡,什么时候可以决定捐献,以及谁应该接受移植。我们的患者也总是愿意尝试新的策略和药物——患者意识到,这个领域已快速地向前发展,他们往往愿意成为推动这个领域向前发展的一分子,以便在未来帮助其他患者。
器官移植与医学其他领域有很大不同。在医学的其他领域,我们毕生都在和死亡做斗争,保护患者免受疾病折磨,或者减轻疾病为患者带来的痛苦。但器官移植却从死亡开始,死亡是我们的另一个起点。
对于那些在名单上排队等待的受捐者来说,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人们期盼着有一个器官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束他们的痛苦,但同时人们也明白,这意味着必须有人死去。很多受捐者会把自己接受移植的日子当作新的生日,与捐献者一同分享新的开始。
电影《修复生命》海报(局部)。影片中,年纪轻轻的赛门,因车祸陷入脑死亡,只能靠生命维持系统活着。就在赛门父母还难以接受事实的当下,医生勇敢告知赛门的生命可以拯救其他垂危的性命,建议进行器官捐赠配对。同一时间在巴黎,一名深受心疾威胁的母亲正在等待心脏移植,赛门的心跳,将为这位坚强母亲注入重生的力量。
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都会死。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在度过漫长的生命之后死去,而另一些人将过早地离去。我们的生命可能会被一场意外、一场疾病或一些看似随机或不必要的事件缩短。我们都要明白,生命不是一种许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活在沮丧之中,或者失去实现某件事情的动力。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珍惜当下,享受身边的世界,拥抱我们的亲人,用爱和同情对待身边的人。
我们应该在高中和大学里对死亡和生命终结问题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基层医疗工作者应该让病人更多地考虑生前预嘱:如果病得很重,他们是否希望医生进行更为积极的治疗?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是否愿意考虑器官捐献?如果家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想要什么,在面对这些决定时,他们就会非常焦虑。
我认为,能够捐献器官拯救他人,延长对方的生命,让他们也可以享受周围的一切,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我们中的太多人,甚至无法赠出这些礼物,就那样死去,这是真正的悲剧。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身边的人,以及我们如何给世界留下一个比我们来到这里时更好的所在?器官捐献就是实现这两点的一种方式。
在器官捐献这件事上,
我们应该独断专行吗?
新京报:这其中显然存在一些伦理或者法律问题——这也是人们所担心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健康捐献者来说。在你的书中,你提到自己赞成活体捐献,但这显然更容易引发伦理或法律问题。
约书亚·梅兹里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充满了伦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器官,必须决定谁能得到它们,我们处于生与死的交界处。
1954年,首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在波士顿进行,由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位,捐献给他因原发性肾脏疾病而命悬一线的弟弟。在当时,并没有长期透析,也没有免疫抑制疗法。也就是说,如果健康的哥哥不同意捐献肾脏给生病的同胎弟弟,弟弟所面临的就是死亡。当时并没有数据显示,捐献者在捐献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会因此更容易出现肾衰竭吗?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这次案例也被称为是“信仰飞跃”事件。
1954年,首例肾脏移植手术在波士顿获得成功。
我将所有活体捐献的案例都看成是一种信仰的飞跃。尽管我们现在活体捐献的成功率很高,但一个人在不需要手术的时候,同意接受手术,将自己置于手术刀之下,割舍器官,这依然是一种信仰的飞跃。对我来说,这些活体捐献者就是英雄。他们通过志愿报名,承担一定的风险去挽救他人。他们就是跑进正在燃烧的大楼中救人的那种人,尽管捐献要比这安全得多,但它仍然是一种无私的表现。
谁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器官捐献这件事上,我们应该独断专行吗?
我们不能让一位母亲或者父亲捐出自己的心脏来挽救他们的孩子——尽管我们自己可能也想这样做。当然,在有良好医疗服务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帮助人们捐出肾脏或部分肝脏来挽救他人。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捐献者应该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和专业的医疗评估,同时,如果他们不想捐献,也不会因此感到压力。
一些早期移植者,如托马斯·斯塔兹尔(ThomasStarzl,肝脏移植之父)和罗伊·卡尔尔(RoyCalne)都反对活体捐献——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手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特别是斯塔兹尔,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与一位失去腿的年轻女性在器官捐献过程中(在评估其血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糟糕结果。
电影《逃出克隆岛》剧照。
在我们现在的年代,手术已经变得安全得多——当然,从来都不会有零风险手术。肾脏捐献者的死亡风险大约是万分之三,肝脏捐献者的死亡风险是平均200到800名捐献者中出现一例,这些都不是零。
有时候,我也会感觉到,给一个不需要手术的人做手术是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的医疗行为,应该是“不带去伤害”的(出自希波克拉底誓词,也称为医师誓词),但对于捐献者来说,他们需要在本来健康的时候冒一定风险。尽管如此,大多数捐献者告诉我,这是迄今为止他们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新京报:健康的捐献者和患有疾病的受捐者间,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会不会涉及道德或经济因素?
约书亚·梅兹里希:活体捐献者不应该承担任何费用。在美国,接受捐献者通过保险支付捐献者的手术费用,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急性并发症相关费用。一些人担心捐献者会因此受到收入上的损失(他们通常要休息一个月),一些政府项目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并不理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不过,捐献者是不允许因为捐献行为获得报酬的,目前这在美国是非法行为。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允许人们向捐献者支付报酬(伊朗是其中之一)。美国一些伦理学家和移植界人士支持这种行为,但他们并非支持有钱的受捐者向捐献者支付器官费用,这些费用应该来自其他途径(比如政府),否则这会加剧医疗领域已经存在的不平等。
电影《逃出克隆岛》剧照。
一些国家存在着非法器官交易,这通常是一种灾难。人们因为贫穷卖掉器官,甚至有时候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得到正常的健康状况评估,事后也无法获得医疗护理。在器官交易中,除了有钱的受捐者成为受益者,移植领域的其他所有人都将受到侵害。
讲述捐献者和受捐者的故事,
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新京报:对于器官移植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哪里?
约书亚·梅兹里希:对于患者而言,移植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器官短缺。希望获得捐献器官(尤其是肾脏)的名单一直在迅速增长,但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并未以同等的速度增长。
当然,最大的问题可能和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无关。当某人突然死亡时,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家人可能并不知道死者的意愿,亲属之间也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因此,我认为,增加有关器官捐献以及对这种无私行为可以挽救生命的教育和讨论,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这些讨论应该在学校、宗教团体、社交媒体,以及支持捐献的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中广泛进行。当人们还健康和年轻时,我们在对于生命终末的选择,包括器官捐献,可以有更多的思索和探讨。
我认为,讲述捐献者和受捐者的故事,并纪念捐献者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这也是我写书的目的之一。一些国家采用了“选择退出”体系(opt-out),假定人们是捐献者,除非他们明确指出自己不想成为捐献者。在美国,我们有一个“选择加入”体系(opt-in),捐献者或其家人需要对捐献进行同意,捐献者可以通过捐献意愿书或进行线上登记。我相信,至少在美国,选择加入比选择退出的制度,更加适合。无论哪种制度,最重要的是教育和讨论,任何人都不应该觉得自己被迫参与了捐献(为了自己或亲人)。我支持捐献,但我也认为,家属必须带着对亲人离世的怀念活下去,需要将捐献看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为。同样,捐献者也是我的病人,我需要感受到,他们希望这成为自己遗产的一部分。
电影《修复生命》剧照。
对于任何外科医生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处理并发症,在我的书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并发症通常会难以处理,有时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有时什么都没有错,但也会出现意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病人坦诚相待,陪伴在他们身边,一起应对并发症,同时,保持谦逊,获得合作伙伴或同事的帮助,确保病人获得最好的结果。
器官移植中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应对那些因过往移植或怀孕,而出现排斥反应的年轻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肾脏移植。一些病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抗体,很难再为他们寻找到一个肾脏。在识别这些抗体方面,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不太能摆脱这些抗体的影响。
新京报:器官移植发展的这些年,外科医生如何提高匹配率?
约书亚·梅兹里希:一个令人惊喜和激动的进展是我们在配对交换项目(活体捐肾)方面取得的进展。想象一下,你想捐肾给你的弟弟,但是他是A型血,你是B型血,你不能直接捐给他,如果我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我弟弟是B型血,我是A型血,那么我可以捐给你弟弟,你也可以捐给我的弟弟。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它也可以适用于有很多抗体的受捐者,甚至能够适用于这种情景:你想成为你孩子的捐献者,但你想给受捐者一个更年轻或更匹配的肾脏。该项目也可以涉及两组以上的捐、受者。
此外,当我们有一位非直接捐献者,或者有人决定捐献到肾脏库中时,该捐献者的肾脏可以启动一个链状流程,即这个肾脏会被传递到有捐献者的病人那里,而他的捐献者的肾脏又会被捐给其他人,如此循环。我们参与过最长的一次,包括了30多个捐献者和受捐者,涉及28家医院,在几个月之间横跨全国。我们是一个名为“国家肾脏登记”的大型配对交换项目的成员,该项目有助于让移植变得容易。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交换项目,让我们的病人获得更好的配型。
对于脑死亡患者,
摘取器官是“杀死”病人吗?
新京报:脑死亡者的器官被捐献给其他患者,帮助其他患者重获新生的新闻越来越多。当脑死亡被法律界定并逐渐被接受以后,在器官移植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约书亚·梅兹里希:在器官移植的早期,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脑死亡还没有真正的定义。当时主要进行的是肾脏移植,一般会在捐献者心脏停跳之后再取出。
1967年至1968年前后,心脏进入到器官移植领域,情况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担心,医生会在他们的亲人还活着的时候,将他们的心脏取出来移植到别人的身上。脑死亡的定义在1968年被列入《美国医学会杂志》,并于1980年在美国成为合法死亡的同义词。公众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接受了脑死亡的概念。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舆论还是法庭,都有一些关于摘取器官是否“杀死”病人的审判。
电影《修复生命》剧照。
虽然大多数医生认为脑死亡是死亡的代名词,但多数民众认为,死亡是心脏的停止。这确实让人感到困惑。许多伦理学家开始质疑脑死亡的定义,以及它是如何与其他不可逆的脑损伤进行区分。
在我看来,所有的法律都是被划定的界限,而脑死亡等同于法定死亡是一条非常合理的界限——这是一种无法恢复的状态,意识已经消失,对进入这种状态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脑死亡不仅帮助了移植领域,也帮助了在重症监护室(ICU)中围绕患者进行徒劳护理的决策制定。它减轻了家属在决定是否继续对ICU中使用呼吸机的患者进行护理时的负担——如果他们已经脑死亡,就没有什么必要做了。
对于脑死亡的捐献者,可以在手术室里,当心脏还在跳动时便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让我们从离世的捐献者身上获得了最好的效果,也让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器官。我们可以从成为DCD(循环系统死亡后捐献)的患者身上摘取器官,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等到心脏停止跳动。这使得我们只能从捐献者身上摘取更少的器官,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更加糟糕的结果。
新京报:捐献的器官对于任何一个受体来说都是一份异常珍贵的礼物,那么,外科医生通常如何对病人进行评估并最终决定一个人可以成为受体呢?比如那些酗酒者——一个患有酒精中毒的病人是否“够格”成为捐献肝脏的受体?
约书亚·梅兹里希:对于受捐者,我们会从医学和社会两方面进行评估。我们需要确保在医学上,可以通过手术达到好的效果,因为器官是极为有限的资源。比如肝脏,我们希望一年的存活率能超过90%,肾脏的一年存活率能超过95%。我们也会进行社会评估,包括受捐者有没有家庭支持,能不能吃药,能不能复诊。如果受捐者不能顾好器官,做移植就没有意义。同时,我们的社工,会在必要时帮助患者尽量获得社会支持。
电影《修复生命》剧照。
对于因酗酒等导致疾病的患者,通常会评估患者是否对自己的疾病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肝脏移植并不是治疗酗酒的方法,如果患者不能控制住自己,或者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危害,移植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
对于这些患者,必须要有移植后接受戒酒治疗的意愿。当然,我们并没有要求受捐者必须在移植前戒酒一段时间。过去曾经要求患者需要在移植前戒酒6个月,但很多患者在这6个月期间就过世了。同时,戒酒6个月在减少复饮方面也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认为,按照疾病本身对病人进行评估,对于医生和医疗系统来说都绝非好的做法。我们相信,一个有着家庭支持,对病因有清醒认识,有主动寻求咨询和强化治疗计划的成瘾类疾病患者,可以带来更好的移植治疗结果。
新京报:对于捐献者呢,也有一些评估标准吗?

约书亚·梅兹里希:对于已故的捐献者,器官采集组织会获得一份社会背景和医疗史、实验室报告(包括传染病检测,比如HIV、乙肝和丙肝)、影像学检查,还有可能包括活检(肝脏、肾脏)。然后,我们会对其质量进行评估。我们将判断这些器官是否适合受捐者。同时,我们也会考虑血型匹配,对于肾脏,还会进行基因匹配。
对于活体捐献者,也就是肾脏或肝脏捐献者,我们会根据其病史、实验室检测值、影像学检查和其他测试,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进行极其细致的分析。我们需要确保他们同意捐献,并了解他们所同意的内容。我们的独立活体捐献倡导者将为他们提供服务,确保他们不会感受到捐献压力,知晓他们没有报酬,同时,还将确认他们真的愿意继续捐献。
捐献者也是我们的病人,
他们和受捐者一样重要
新京报:器官移植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约书亚·梅兹里希:一般来说,在移植后马上就开始工作的器官越关键,我们就越想快点移植。
对于心脏、肺和肝脏,我们一般会在捐献者手术的同时开始受捐者的手术。肾脏和胰腺的移植可能会被推迟,不过我们会尽量在24小时内将它们移植进患者体内,如果可能的话会更快。
我们开始在一些器官(心脏、肺、肝脏、肾脏)上使用新的泵送技术,这使得我们可以在观察器官功能时,推迟移植(几个小时),甚至修复一些功能障碍的器官。
对于器官移植而言,一个采集团队里有很多成员:外科医生、协助手术的技术人员、准备好灌注液并与受捐者的医院和外科医生沟通的协调员,以及与移植名单一起组成的所有团队的协调员。我们还有飞行员(我们使用的是固定翼飞机,但有些项目使用直升机),运送我们往返医院的司机,以及协助我们在供体和受体手术中进行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和擦洗技师。此外,胸部(心脏、肺)和腹部器官可能会有单独的团队。整个过程中,参与的人可不少。
新京报:在器官捐赠和移植中,你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约书亚·梅兹里希:在与捐献者家属交谈的过程中,交织着很多情绪,比如感激、谦卑、悲伤,但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为捐献者家属提供帮助,帮助刚刚过世的人准备这份遗产,也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温暖。
我认为,捐献者也是我们的病人,他们和受捐者一样重要。对我来说,最有感情的是我的第一位捐献者。当我到达捐赠医院和家属交谈时,大约有15个人在那里。我很紧张,担心家属们会把我看作是夺走他们挚爱之人的秃鹫。
但我完全错了。他们一字一句地追问,想知道器官捐献的整个过程,想知道谁会获得器官?什么时候进行移植?他们能见到受捐者吗?然后,他们告诉我,这个刚刚去世的男人,他喜欢做什么,喜欢去哪里,谁爱他。
当进行器官摘取手术时,我们总会默哀一阵。在那个时刻,我们会去想,这个捐赠者是谁,通常会读一些由家属提供的东西,可能是一首诗或祷文,也可能是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或回忆。然后我们转换自己的情绪,确保尽最大努力安全地将器官取出。对我们来说,这种心情相当复杂。
基拉在因车祸离世后,父母将她的心脏捐献给了等待移植的马克思,手术非常成功。图片来自于BBC。
我认为,与捐献者家属交谈是我们在移植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些捐献者的遗产保留下来。我并不认为,捐献者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需要接受移植的人能够得到移植机会。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更多捐献者在献出这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让他们的死亡变得有价值,也让捐献者的家属们感受到一定的意义。
我见过一些捐献者,父母们就在房间里,对他们因意外离世的孩子告别。显然,我们不能让他们复活,但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们的死亡带去一些意义。我们的移植病区里有一张照片,一位母亲戴着听诊器,听着10年前离世女儿的心脏,在一个接受移植的年轻人胸腔里跳动。她在哭,他也在哭。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我眼里都会充满泪水。
校对丨危卓